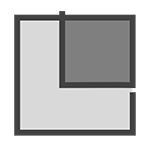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之中,商业是这个世界的主要社会活动。在这个世界中,人要到社会之中,来满足他各种各样的需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又是我们恐惧的根源。因为我们感到与这个世界相处是不容易的。这个感觉很深,坐落于我们灵魂的深处。但除了恐惧,我们对这个世界也有所期待。我们从个体自处的境地走到世界中,并不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告诉这个世界一些什么、也希望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所以,个体究竟如何和社会相处?个体究竟在社会中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之一。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我们被告知有一种特殊的人类价值,叫做“个性”。坊间有一种意识形态宣教告诉我们说,不用在乎别人的眼神,我们依然可以过得很好。但是,狄德罗在《自然之子》这部戏剧中,借剧中人物之口,说过这样一句话:好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而坏人总是孤独自处。正是因为这本书,狄德罗和卢梭分道扬镳了。他们曾经是关系非常要好的一对好基友。因为卢梭采取了另外一种看法。卢梭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孤独的。所谓孤独的人,是说人的本性。自然人游荡在原始森林之中,处于wandering这样的一种状态中。自然人不会和他人有意识地坐下来。当自然人和他人有意识地坐下来的时候,人就已经离开了自然人的状态,进入到一个社会状态。人性的堕落就是从一个人愿意和另一个人坐下来过社会的生活开始的。
我们今天去思考个体如何与社会相处的问题时,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从人性体验上来讲,都要格外注意一个问题。我们有时候确实非常认可现代个人主义思想中的许多观点,特别是认为存在一个本真的自我,而本真自我所构造的那种有个性的生活,被认为是我们个体生活意义的最终来源。但是当你在知识世界,或者真实的现实世界中,越来越多地体验和经历后,你可能会发现,你的思想世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道理,迫使你不得不重新思考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就是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究竟如何自处?我们到底能不能在社会中过一个孤独自处的生活?今天的这个讲座,总体上就是围绕这个问题来展开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到这个主题之中。
我想最好从同学们比较喜闻乐见的话题开始。有多少同学读过《三体》?(一个同学举手)有一个同学读过。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三体人和地球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除了他们能脱水之外。(同学答道:“三体人的思维,就是他的话语,是通过看到对方的思维来进行沟通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人类为什么思维和他们的话语是不连接在一起的。”)嗯,非常好,非常好!
三体人有一个地球人根本没有的特征,就是三体人他所想的东西能够直接显现出来。他不需要通过一些更复杂的机制,把自己所想的东西和另外一个三体人进行交流。这个特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三体人与地球人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性。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设想,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怎么在人类社会之中过社会生活的。我们需要和他人交流,对吧?当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想的东西经常不是我们口中所讲的东西。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心里所体验的内在情感,并不是我们外在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回应方式。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一个人性事实,就是“我永远无法看穿他人”。如果我隐蔽得足够好的话,他人也无法看穿我。但三体人和地球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三体人是彼此看穿的。对于一个三体人来说,他所想的东西,直接就展现给了其他三体人。没有任何时间上的迟滞,没有任何隐瞒的可能性,甚至不需要做出隐瞒的努力,就自然地显现出来了。所以,在人性受到一种深刻的自然必然性束缚的地方,三体人是不受约束的。这个自然必然性是什么呢?就是对他人的内心世界,我永远也不可能彻底了解。所以,“他心问题”只是一个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哲学问题。对三体人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人永远无法看穿他人,这是一件非常严峻的事情。
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在这个世界中,如果我在内心中需要别人真正理解我,那么我会发现我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因为别人不是我,所以别人难以了解我。更糟糕的是,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看穿,我们不仅不了解彼此,而且我们彼此嫉妒,有的时候甚至彼此莫名奇妙地憎恶,把他人想得很坏。鲁迅先生说,“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人”。一旦我们对某些共同的标的物产生了兴趣,比如打算追求某种独一无二的荣誉、东西、物品,我们彼此之间就处于一个彼此不知道内容、方式和过程的算计状态之中。人性的这个彼此不能看穿的特点,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现代生活处境。那就是,每个人都像“单子”一样和他人在一起过着孤独的、在内心世界中离群所居的社会生活。在这种生活处境中,如果社会生活没有得到很好地设计,那我们每个人之间必然是互相猜忌的、互相怀疑、互相敌视的。但即便社会能够得到很好的设计,那么也只是降低猜忌、怀疑和敌视的程度而已。本质上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猜忌,互相怀疑,互相提防的世界之中。这个图景就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要给我们刻画的所谓现代社会的图像。霍布斯之所以给我们刻画这个图像,是因为他抓到了人性中最深的一些特征。也就是我们既无法彼此看穿,又不得不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在一起”。正因为“不能彼此看穿”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约束,所以看起来,人的真正的生活,好像只能是他自己内心拥抱的那种属己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一方面,我们确实彼此需要的、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彼此而生活。假装成好像是在过社会的生活,living together。但另一方面,我们内心是孤独的、个体化的、彼此之间分离的、散落的。
我们人类属于自然世界,自然世界在构造我们时,赠予了我们社会生活的需要,同时又夺去了我们看穿他人的能力。个体和社会的张力难以消弭。我们究竟该如何提出一个更好的政治制度安排和统治秩序设计,使得这个张力不要那么的尖锐,甚至有所缓和?在很大程度上,整个近代政治哲学史,是在这样一个解释事业的基础上构造出来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近代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
自然世界如此特别,它构造出我们的人性,也使得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尽管我们的内心世界无法被人看穿,但在内心最深的地方,我们对于他人的需要是我们自己无法满足自己的。当我们需要他人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他人才能满足我。而他人是不是真的在满足我,这件事情,我无法判断。在这个世界之中,你永远可以怀疑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是不是真的像你所需要的那样,满足了你的那个需要。比如说你对友谊的有一些需要。那么你要求的是什么呀?你要求有一个对象,是你真正的朋友。而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朋友?你没法看到。你无法像看底牌那样洞悉他人的心。
不仅如此,现代世界又是一个如此特别的世界。如果你们的马哲老师给你们上课的话,他可能会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如果从一个纯粹的哲学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说现代世界本质上来讲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和谁打交道,也永远不知道跟你打交道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在现代世界中,我们越来越无法真正了解我们要打交道的对象。我们进入到了一个不断跟人相遇、却越来越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处境之中。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世界中的人格外孤独。
但孤独并不是一个有内在价值的事情。当我们说现代人的生活是一种孤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找到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去改造现代世界的样貌,帮助现代人摆脱这个孤独的处境,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充满温暖、充满爱、充满感动,带给生活某种属人生活的厚重性。问题是,怎么去改造它呢?你们可能知道,当代伦理学里有一些向古代思想复归的理论冲动。一些思想家觉得,现代人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呼吁了一种重新理解生活本身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试图把我们带回据说我们曾经活过的那个样子。让我们用一种据说曾经活过的生活姿态,来重新安顿我们现在正在过的生活。我们在很多学者身上能够看到这种“还乡症”式的理论冲动。这些学者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时代,在其中,人是真正过生活的,bios。据说这种生活形式是繁荣的,在彼此互相了解的、小规模尺度上的公共空间中展开。人们通过谈话、通过交流、通过辩论、通过协商,来达到一种共同的体验、共同的知识确认,从而达到对公共真理的共同掌握的境界。这种生活被称为是城邦的生活、古代的生活。它属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想象中的那种理想的生活样式。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不是真的生活在这样一个生活世界中。它是虚构的,只是一个生活理想,同时也成了当代人“还乡症”梦想的对象。
有病当然还得吃药。但“还乡症”的思路,本身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因为它提醒我们注意到克服彼此无法看穿所带来的深深的孤独感的一个可能方式。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我们的社会生活理想是“生活在一起”,那么不如让我们真正地“生活在一起”,而不要明明只是“凑在一起过”,还假装“生活在一起”。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谈到友谊的时候,他说真正的友谊要求朋友整天彼此相处。为什么要整天彼此相处啊?因为真正的友谊的获得,必须要克服彼此无法看穿的自然必然性的束缚。只有整天彼此相处,我才能够尽可能看明白你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这个想法的意思是非常清晰的。在近代世界、现代世界中,许多思想家实际上多多少少是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曾经设想过解决现代社会弊病的一个方案。就是让我们回到田园牧歌式的、类似于古代城邦的那样一种小尺度、小规模的、small-size 的封闭的共同体生活之中,来过一种类似于城邦生活的现代生活。持这种思想的,简单的说一下,像哈林顿,再比如说,美国立宪时候的某些反联邦党人,等等。这些思想家多多少少都认识到,只要我们能够真正地“生活在一起”,那我们就可以克服现代生活的某些弊病。当然,其中之一就是现代人深深的孤独自处的处境。
但“还乡症”终究是病,所以存在着问题。首先,这样的一种生活形式是抽象出来的,是理想化出来的;其次,更严重的事情是,那种生活依赖于一些非常独特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现代社会已经失去的。比如说,在希腊世界,如果要过上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朋友的生活、公民的生活、城邦的生活,它的必要条件是,一定要存在人数众多而且不自由的奴隶。亚里士多德讲,只有摆脱了一切形式的自然必然性的生活,才是真正属人的自由的生活。自由生活的意思就是摆脱了自然必然性的那样一种生活。实际上,在自然必然性之下,不仅没有“自由的生活”,连“生活”都是没有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摆脱自然必然性那样一种状态、一种生命的状态。所以,可想而知,小尺度的生活、彼此熟知的生活,要求的是全身心地、全神贯注地参与到共同体构造之中。因此,一个人为了过“生活”,他必须把生产、把对物质需求的自然必然性的克服交给另外一些人。古典古代设想的是交给奴隶。马克思设想的是交给机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去过属人的生活,让机器去替代人劳动。
不仅是这两点,更重要的是,古代人的自我理解方式,现代人也不一定继续采取。古代人怎么自我理解呢?我们都知道古希腊有很多的戏曲艺术形式。我们中国非常晚、可能要到南宋才有。比如说悲剧喜剧史诗的观赏。我们都知道古希腊世界是有剧场的。剧场有很多的功能,其中之一就是看戏。看悲剧,看喜剧。在很大程度上,柏拉图是一个戏剧作家,他的作品本质上就是以戏剧的方式来表达的。古希腊人在看戏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在消遣娱乐,与现代人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式看戏不一样。古希腊人去看戏的时候,去剧场看悲剧、喜剧或者史诗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去那儿受教育。在什么意义上他是受教育的呢?就是他实际上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进入剧场。戏剧通过内在张力的呈现,通过对于人类生活的悲剧性处境的揭示,展现给观赏者一个全新的、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经验过的视角。一个想象的视角,一个反思的视角。那么观赏戏剧的人呢?他站在这个想象性的视角中,获得一个契机,来反思自己带进剧场的那种生活体验,从而对自己的生命处境有一个新的认识。戏剧,在再造欣赏者的生命经验的意义上,是发挥教育功能的。比如说你对朋友做错一件事情,去看一场戏,回来以后有了新的认识。第二天和你朋友相处时,你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智慧,希望能够把之前的那种不和谐的相处方式克服,达到一种新的相处的状态。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则变得有点特别。我们处于这样一个芸芸众生来来往往的世界,很多陌生人之间此生不会再见对方第二次。共同反思的需求不是那么紧迫,共同反思的能力慢慢也会退化。“还乡症”幻想的古代生活,如果不是虚构的话,起码也是回不去的。我们可能不得不要长期忍受生活在霍布斯所刻画的那样一个现代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跟自己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永远不知道他的内心处境究竟是怎样、他正在究竟遭遇什么样的改动心灵的事件、正在承受什么样的生命内在体验、即将走到什么样的地方。
但是,毕竟,一旦现代人试图去追问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带到一个处境之中。在这个处境中,生活意义的构造需要他人在场。不过,他人的简单在场并不能满足我们生命厚重性的需要。当我需要把那些最深的生活经验拿出来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去和别人交换我们的生活体验、甚至试图听取别人从他的视角所提出的对我的生活经验的理解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人的简单在场,不能够足以满足这个需要。那么怎么办呢?
在这里,可能有同学就会说,OK,我可能不了解你,我甚至可能永远也不能真正了解你,那么,不如我做好自己,做一个真诚、诚实的人好了。这样起码可以保持我的内心的高贵和诚实。但他这么做之后,却发现尽管他对所有人敞开了心扉,但所有人都不能够理解他、甚至误解他。于是,他责怪这个世界:我已经把心掏给了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正常的回应?没有接受我掏出去的这颗真诚的心?他觉得他把自己内心最深的想法和感受告诉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没有接纳。那他该怎么办?
这种情况其实对同学们来说并不陌生。对吧?很多同学都有这样的体验。于是,我们就发现,这种体验某些时候就导致有些同学变得很孤僻。所谓孤僻是什么意思呢?用哲学上的语言来说,就是他开始倾向于过一种狄德罗所说的孤独自处的生活,退隐回一个不寻求外部理解的内在生活之中。当他认为这个世界不能够去回应他内心最深的想法和感受时,当他被世界频繁地误解甚至中伤时,他觉得,他对世界应该采取一种拒绝的态度,去过一种孤独自处的生活。这样一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在思想家中并不少见。对吧?比如说,有谁啊?(听众中有同学说尼采)尼采。然后呢?(听众中有同学说叔本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不是这样的人吧?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我这学期在上一门课读他的书:卢梭。
卢梭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把他拿出来说一说呢?因为卢梭认为他自己是个很真诚、很诚实的人,他的真诚就是,他觉得他已经把他的那颗心、把他心中所想的一切,都交给了这个世界了,但是,这个世界要么漠然视之,要么就是背叛了他。这个世界是怎么背叛他的呢?卢梭觉得,当他把所有想法都真诚、诚实地告诉了这个世界以后,这个世界用一个巨大的阴谋来回应他。卢梭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与他为敌。最大的敌人是伏尔泰,第二大敌人可能是狄德罗。
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什么问题呢?我想说,如果我们渴望在这个世界中获得他人的承认和理解,通过他人的持续在场来增加我们生命体验的厚度,那么,简单对这个世界报以真诚或诚实的态度,是不够的。卢梭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人,如果认为他自己是诚实的,那么,仅仅这一点,并不能使他的生活充满意义、变得厚重起来,并不能使他克服人性中由于彼此无法看穿所带来的深深的孤独感。No way!为什么会这样?我真诚地面对世界,为什么不能成为自我厚重的生活意义的来源呢?毕竟,我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我告诉别人我心中所想的东西,我是一个如此诚实的人!难道诚实不是一个美德吗?
也许真诚、诚实并不就是一个美德,起码不是至高的美德,因为真诚本身并不就是真理。举个例子来说(这是我十年前从吴增定老师那里听来的)。比如说有一天,假设你是一个男同学,在街上看到一个美女,你过去说:“美女,我想强奸你。”你确实是那么想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事情,是吧?你真诚、诚实地宣告了你内心中的别人根本无法看穿的那个部分。但是诚实不是真理本身。如果真诚是一种至高美德,那么它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恐慌。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干脆不要诚实了?我们去过一种彼此文质彬彬、以礼相待、温良恭俭让,但是永远不让别人看穿自己,永远让别人觉得自己在行为上符合了文明世界一切要求的那样一种生活,好不好?看起来,你很nice,但在真实的内心中,谁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样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会过得更好些?
卢梭确实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当他说自己很诚实地面向世界诉说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crazy的人。当他疯狂地批判这个世界的虚伪、造作时,批判文明人用对德行的服从代替了对美德真正的向往,批判现代社会中人们用外在行为的一致取代了内心中的崇高和良善的时候,我觉得卢梭是一个非常天才的思想家。如果别人无法看穿你,于是你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封闭起来,不以真诚的方式去对待别人,不以诚实的姿态去对待别人,那么你能得到的是什么呢?你能给予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呢?是各种各样的看起来很和谐、看起来很一致、看起来彼此认可的表象。但其实在内心深处,大家都知道大家是假的,你知道你是假的,他知道他是假的,你知道他是假的,他也知道你是假的。于是产生了一个共同意识,就是我们都是假的。我们过着虚假的生活。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彼此之间,生活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已经有了的也很快被掏空了。现代虚无主义,尤其是价值虚无主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生活中的这样一个处境。我们每一个人都笑脸相迎,但彼此之间互相仇视。每一个人都表现得好像把别人当作人一样尊重,在内心深处却把他当作算计的一颗棋子。所以,我们在内心深处不相信别人,也不在乎别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彼此相信、彼此在乎的。卢梭对于一个冷漠的丑陋的虚伪的现代世界的批判,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洞见。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crazy的卢梭。卢梭一方面揭示所有的虚伪;另外一方面试图保持对于这个世界的真诚。当他真诚到认为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好人的时候,他发现他被这个世界抛弃了。孤独自处的卢梭,并没有获得生活的意义,变成了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哲学生活最糟糕的地方莫过于如此。我刚才跟一个同学说,学哲学是个非常危险的事。如果你试图在哲学中找到一切能让你得到慰藉的东西,特别是情感性的慰藉,我觉得很可怕,很容易走火入魔。更可怕的是,如果你采取一种理性至上的姿态,认为基于理性的探究方式能帮你解决你所有的人生处境方面的困惑,这更是极端危险的。卢梭就在这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他认为这个世界已经抛弃了他,他如此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心都掏给了世界,但世界把它丢给了狗。
今天有很多本科同学。我听说现在很多同学在自己的宿舍都装上了床帘。(同学:对呀!)对此我很不理解。很多同学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宿舍曾经围绕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发生过矛盾,彼此之间都觉得对方坏透了。彼此都觉得自己那颗幼小、充满良善、美德的心被伤害了!每个人都觉得他自己的观点是代表了正义、良知、美德的,都相信自己是诚实的,而且自己的诚实蕴含了真理,是来自正义女神的声音。所以,一旦这个世界拒绝了自己的声音,那么这个世界必定就是一个糟糕的世界。因为它拒绝了良知,拒绝了正义。自己作为正义、良知的化身,只能采取决绝的办法——买帘子,把自己同这个世界隔绝开来。从卢梭那么伟大的天才到我们日常琐碎的生活,讲了这么多,就是要告诉你们:把自己同世界隔绝起来,或者自我加封为良心的化身、视不能接纳自己的他人为地狱,是解决不了现代人的孤独处境的。在这个意义上,狄德罗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好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坏人却总是孤独自处。
我们很多同学对伦理学有兴趣。有一种非常糟糕的思考伦理问题的方式,就是总是试图从生活的外部构造一个规范体系,然后站在生活外部的立场上,站在这个虚构的规范体系中,去对生活本身指指点点。这种方法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阿玛蒂亚·森在批评罗尔斯的时候,说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一种先验判断论的正义观,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理念论思维方式的要害所在。
讲座前有些同学通过另一些同学问我,今天来是不是讲伯纳德·威廉斯?我说不完全是,虽然有一些想法确实来自于威廉斯,但因为是个科普型报告,所以也并不只是介绍威廉斯的观点。但不管怎么说,伯纳德·威廉斯的许多思想我是高度赞同的。我非常喜欢威廉斯,因为他不断地提醒我们,人性相关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活问题。不可能通过构造一个生活之外的规则体系来加以解决。
如果有同学确实跟卢梭一样,觉得自己已经把心掏给了这个世界,但是世界把它拿去喂了狗。这时候需要停下来的不是这个世界,需要停下来的是你自己。你绝不能允许你的思想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下一步了。因为下一步,你就会认为,你跟这个世界之间的紧张,是正义与不义,善良与邪恶,良心与愚昧,体制与反体制的较量。我们每一个人在本能上都有一个虚伪的本质。就是我们总希望我们的想法,无论它多么的荒谬,都是以道德的名义发出的对于这个世界的最高贵的怒吼。在心理上,以此来使自己的行为获得价值崇高感,来确证自己即使是少数派也仍然掌握了真理、是一个正义的少数派。这是我们生活中最糟糕的一个情况。我觉得狄德罗的话就是当头一棒槌。因为他告诉我们:坏人,都是孤独自处的,好人才生活在社会之中。所以说,当你有一种道德优越感,觉得可以有一个外部观点,可以对包括自己生活在内的一切人的生活指指点点的时候。你要小心啦!很危险。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用一种多重视角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跟我们想的可能不一样。人们不能彼此看穿。如果你不是从“我不能看穿别人”这个角度来理解问题,而是真正把这句话理解为人不能彼此看穿的时候,你发现你得到了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这个世界飘荡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好几十亿,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彼此之间都不能看穿。你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在这个世界中,如果人们彼此之间都不能看穿,但每个人都有自己彼此的生活,那么如果你没有充分的证据假设他是不真诚的,你首先要假设他是真诚的。否则你太坏了,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人。
真诚本身并不一定是生活的价值源泉,它只是生活的一种形式。不过,只有当我们预期他人是真诚的,那么我们才都够坐下来彼此之间交流一下、谈一谈。进入到什么样的交流状态之中呢?进入到构造共同生活的那种交流之中。什么叫构造共同生活呢?比方说你们班有50个人,50个人有50种生活。但是还有一种生活是和这50种生活不一样的,叫班级生活。班级生活是非常独特的,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班级生活需要大家一起去创造。同样的道理,国家也是一样,社群也是一样。我们要一起创制我们的共同生活。生活是一种发明,共同的生活更是一种发明。在这样的情况下,真诚只是共同生活的一个要件,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得到一些“厚”的支持。厚的、能够分享的共同生活经验必须进入到生活的真诚形式当中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带着那种彼此公认的、能够真正加以接受的价值原则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为什么中国的公共讨论通常总是一个失败的事业?因为它总是立场优先的。一些人说他自己代表了良心和自由,另外一些人被他们指责为代表了体制和保守。意识形态选边站,那真正严肃的问题就没法讨论了。如果我们意识到,价值原则只能来自于生活本身,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倾听彼此的生活。我太太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最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他们班有一个同学,每次说到“毛主席”的时候,都热泪盈眶。(同学笑)我跟我太太说,你有没有倾听过她的生活经历?问问她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背景?孟德斯鸠在这里就很重要了。他很英明的指出,山边长大的,平原长大的,想法都不一样的。所以要倾听别人的生活,不要总是站在一个外部的观点上去评价人、论断人,这样你才能够和别人一起去创造共同生活。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生活经验的交流,并不是大杂烩。生活经验的彼此交流并不是一个纯粹叙事的过程。比如说一个人如果跟我描述他自己的生活,当我跟他分享他的生活经验的时候,我并不是在简简单单地接受他对他生活处境的叙事,narrative。并不是这样。我实际上跟他进入到一起共同反思他的生活描述的过程之中。在这种互相交流生活经验和对于生活本身的看法之中,我们构造出一种评价和规范的要素。规范和评价的要素不必非得来自于一种外部的观点,完全可以是生活之中创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都喜欢“八卦”。在“八卦”描述中,不仅仅是narrative,不仅仅是在叙事。
所以,规范性的要素是可以从生活本身中鉴定出来的。我认为这是伯纳德·威廉斯所要告诉我们的最深的道理之一,也是伯纳德·威廉斯为什么重要的原因。从外在于生活的角度来构造规范性的思想,本质上来说是非常brutal的。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这本书里,伯纳德·威廉斯在第三章要讲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从外部的观点来建构一个评价生活的规范性立场,这是非常brutal的。生活完全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反思生活本身的规范性要素。因此,当我们去创制我们共同的生活的时候,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要真诚的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掏出来,跟大家分享,创制一种共同的新的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可以真诚的生活,而且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有一种价值的厚度。就是说,只有这样,我们才终于知道我们的真诚生活到底是不是具有真理性的、到底是不是对的。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卢梭的“真”和一种不同于卢梭的“对”。卢梭认为他的生活是很真诚的,因为他主观地判断,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对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最深的情感的宣告。他认为他的生活是“对”的,因为他自认为他真的宣告了他自己内心关于这个世界所想的观点。所以这个“真”、这个“对”,都是他自己从第一人称立场自我鉴定出来的。但这个想法的残暴性恰恰就在这里:“真”的判断和“对”的判断都是他自己做出的。一旦这个世界不能够接受他的关于“真”、关于“对”的定义的时候,从他的第一人的角度来看,错的是谁啊?这个世界!狄德罗可能要告诉我们的是另一个图式的故事,就是我们的“真”的、我们的“对”,都是我们共同构造出来的,“真”只是我们的一个态度,“真”只是一个非常形式的东西。我们只是为了“生活在一起”,而发明构造了一个属于我们的“真”和“对”。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拥有良心的人,那么要到社会中去获得良心的内容。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真诚的人,那么要到社会生活中去获得真诚的定义。第一人称的宣告只是一种形式的确认,是面向自己的确认。但是真诚的、真实的内容,良心的内容只有社会才能帮你建构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人和他的生活是不可能离开社会,不可能离开社会世界的来获得定义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把我们为己的属性,和为人的属性统一起来。
这也说明,一个纯粹第一人称视野中定义出来的“自主性”,很有可能是一个幻觉;说明从第一人称视角得出的有关自我的反思知识,很有可能是一个幻觉;说明一个人试图只是面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内在情感来保持自己的真诚态度,很有可能是一个幻觉。为了彻底打破这个幻觉的幻象因素,我们恰恰就需要进入到生活,进入到真正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彼此交换最深的生活信念、生活知识、生活体验的那样一种社会世界的生活之中。
如果我今天讲的是有道理的,那么这对于我们理解政治世界的构造、理解公共领域的可能性,会有一些启发吧。概括起来说,我的观点所反对的,就是在政治哲学中,那种诉诸“实践理性”这样一种先验判断论的哲学概念来理解政治的道德本质、公共生活的道德本质的那样一种观点。因为我的观点所相信的,是另一种理解政治、理解道德、理解人类价值的图式。这种图式,是“自下而上”的,是从生活本身的土壤之中来构建规范性要素的。而不是像时下比较流行的思想方式那样,在思考政治、道德和人类价值的时候,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从一种理想的、先验的原则出发来提出指导生活本身的原则。我反对在人类生活的复杂性面前采取这样一种简单的思想方式。
所以,作为一场科普讲座,我没有给你们灌多少“鸡汤”。但如果一定要撒把“鸡精”才能算哲学科普的话吗,那我想这样总结这场讲座:如果在生活中,你还有一个真诚性的自我要求的话,那么只有与他人分享你的生活,摆脱你厚重的孤独感,通过他人来定义你的“自我”,你才能够真正克服自然必然性束缚你的枷锁。换句话说,“还乡症”的方案,既虚构了一个普罗米修斯的圣火,也缔造了一个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它假设有一团圣火,能够通过“还乡”的方式,利用普罗米修斯的姿态来获得,但这是虚构的。然而这个神话也隐藏了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就是,普罗米修斯的圣火就在我们彼此的生活之中。如果你能够用真诚生活的态度形式,来和别人分享你的生活经验、生活信念和生活原则,那么我想普罗米修斯的圣火就在我们彼此共同开展的生活之中。“生活在一起”,你才可以得到一个厚重的自我理解,构造出一个既属于自己、又属于社会世界的坚实“自我”。孤独的自由并不美好,因为本真的自我空洞晦涩。我想这是这场讲座的结论所在。